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昨天作為北京金融法院的特約監督員有機會旁聽一個證券虛假陳述民事賠償的案件,金融法院法官專業度非常高,對核心問題總結到位,理解深刻。出于保密義務,不去討論具體案件,就此類訴訟中幾個非常重要但尚有爭議的普遍性問題談一點看法。
第一就是民事賠償和行政處罰的關系。雖然現在取消了行政處罰作為立案前置條件,但是絕大多數案件還是處罰在先的。但是一旦處罰,不少法院就自動啟動按比例連帶模式,認定責任。但是這里要反思一個問題,有行政處罰就一定有民事責任嗎?這不僅是“重大性”的問題,而且更是應當辨析行政責任和民事責任法律邏輯的根本不同。證券虛假陳述民事責任本質上還是侵權責任,只不過特殊在推定因果關系推定過錯,但行政處罰的邏輯是違規,這里的規包括很多規范性文件甚至操作指引。打個比分說,好比醫生做手術,必須嚴格按照規定程序,任何一步只要錯了,哪怕沒結果,也可以甚至應當“處罰”,但雖然可能跳過了其中一些步驟,只要沒有不利后果,就不應承擔民事責任。所以行政處罰不能直接推導出一定承擔民事責任,雖然大多數是結果競合的。
第二是比例連帶模式反思。經過若干案件探索,中介機構按“比例連帶”連帶模式承擔責任似乎成了一個黃金法則。因為這太符合正常人的思維習慣了,邏輯起點是“你總有點過錯吧?!”,然后是“你有過錯多少要擔點責任吧?!”,最后是“我只讓你擔百分之五夠意思了吧?!”。但是作為專業人士,不能僅因為這個邏輯舒服而停止思考,比例連帶始終沒有說清楚共同侵權的合意在哪里,特別是中介機構只是一般“違規”而非明知且合謀的情況。另外,券商和會計師百分之百連帶,經常成了破產發行人的替罪羊,也非常不公平。深圳中院在保千里案件中采用的補充責任模式,仍然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和經常是更合理的做法。
第三重大性尺度的主觀性。過去對重大性這一點在司法實踐中感覺重視不夠,新的司法解釋出臺后,這一點有很大突破。上海地區有幾個突破性判例非常值得關注。但是感覺重大性的尺度相對比較主觀,另外法院面對重大信息披露不實,僅從量價變現不大來否定重大性還有很大顧慮。這估計也是個會長期存在的問題和爭點。
第四就是虛假陳述民事賠償訴訟的有效市場假說理論基礎和新三板、債券等明顯非有效市場之間的矛盾。雖然最高法院債券審判紀要努力做了差異化對待,但是新三板和債券領域的根本矛盾并沒完全解決。
除此之外當然交易因果關系,損失因果關系,三日一價,損失準確計算(包括是否扣除以及如何扣除系統性風險和非系統性風險),也都有很多值得探討和尚待厘清的問題。
另外一個參與各種訴訟仲裁的觀察和體會是,律師水平對一個審判的影響還是非常大,法官有嚴格紀律,特別對金融法院這種專業法院,法官總體都很專業,出現水平層次不齊的概率較低,但是律師卻是海選的,經常水平層次不齊,各種大跌眼鏡的事也是經常可以遇到,有時候一個水平差的律師也可以攪亂一個法庭。
出差車上粗淺思考草就一貼,三月的廣州沒有見到春日陽光卻遭遇陰雨連綿,但仍慶祝終于從過敏性鼻炎和頸椎病雙重夾擊一個月的痛苦中活過來可以正常寫字工作了,感謝中醫。
關鍵詞:
 蘋果公司開始對合同工進行裁員?據知情人士透露:公司已悄悄開始削減合同工數量 【 蘋果公司開始對合同工進行裁員 】 財聯社2月17日電,到目前為止,蘋果避免了亞
蘋果公司開始對合同工進行裁員?據知情人士透露:公司已悄悄開始削減合同工數量 【 蘋果公司開始對合同工進行裁員 】 財聯社2月17日電,到目前為止,蘋果避免了亞
 潤建股份:3月24日公司高管許文杰、梁姬減持公司股份合計84.9萬股 證券之星訊,根據3月24日市場公開信息、上市公司公告及交易所披露數據整理,潤建股份
潤建股份:3月24日公司高管許文杰、梁姬減持公司股份合計84.9萬股 證券之星訊,根據3月24日市場公開信息、上市公司公告及交易所披露數據整理,潤建股份
 全速域超強動力拉滿駕駛樂趣,瑞虎7 PLUS 新能源兼顧高效能與高性能 車企最卷之年,新能源尤甚。日前,奇瑞瑞虎7 PLUS 新能源正式上市,以超強動力強勢
全速域超強動力拉滿駕駛樂趣,瑞虎7 PLUS 新能源兼顧高效能與高性能 車企最卷之年,新能源尤甚。日前,奇瑞瑞虎7 PLUS 新能源正式上市,以超強動力強勢  捷克前總理伊日·帕勞貝克先生成為天獅集團特別顧問|天獅直銷|天獅李金元 11月10日,天獅集團歐美業務部歐洲區總經理李愛軍先生在捷克分公司接待了捷克前總理伊
捷克前總理伊日·帕勞貝克先生成為天獅集團特別顧問|天獅直銷|天獅李金元 11月10日,天獅集團歐美業務部歐洲區總經理李愛軍先生在捷克分公司接待了捷克前總理伊  天獅集團:在合作共贏中抓住機遇|天獅李金元|天獅直銷 2020 年,全球經濟放緩的速度比大流行以來以往任何一次全球衰退都要慢。 縱觀全球,
天獅集團:在合作共贏中抓住機遇|天獅李金元|天獅直銷 2020 年,全球經濟放緩的速度比大流行以來以往任何一次全球衰退都要慢。 縱觀全球,  天獅集團:“三全四真”戰略尼日利亞宣傳|天獅李金元|天獅直銷 2023年,非洲及中東事業部總裁賈永清先生為貫徹落實天獅集團董事長李金元的戰略構想,
天獅集團:“三全四真”戰略尼日利亞宣傳|天獅李金元|天獅直銷 2023年,非洲及中東事業部總裁賈永清先生為貫徹落實天獅集團董事長李金元的戰略構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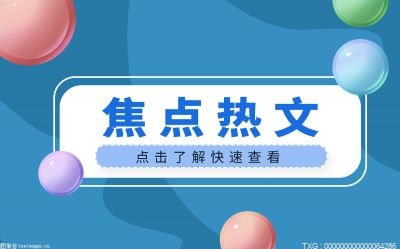 一招短線選股法是什么意思?尾盤買入法的好處有哪些?拉尾盤什么意思? 尾盤買入法:屬于短線的操作,今天買了,明天就有機會賣的。每天下午14:30分的時候有
一招短線選股法是什么意思?尾盤買入法的好處有哪些?拉尾盤什么意思? 尾盤買入法:屬于短線的操作,今天買了,明天就有機會賣的。每天下午14:30分的時候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