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說寫作由素材到半成品到藝術(shù),這一過程如泥制成坯燒成陶,如米煮成飯釀成酒,陶是泥的“藝術(shù)”,酒是米的“藝術(shù)”,燒制火候與蒸餾發(fā)酵促成了這一根本性的轉(zhuǎn)化。同樣,小說藝術(shù)的誕生因可控和不可控的因素諸如經(jīng)驗、技巧、才華、靈感等的參與,其過程變得既混沌模糊又有跡可循。
那么,究竟是什么促成了素材或事件向小說藝術(shù)的根本性轉(zhuǎn)化呢?這一異常繁復(fù)又指涉小說本質(zhì)的問題總是誘使一些文學(xué)理論家去一探究竟。許多年以來,這一秘密似乎正從各個方面被揭示出來。比如我們熟識的一些理論有:俄國評論家什克洛夫斯基說:“藝術(shù)的技巧就是使對象陌生化”;法國的羅蘭·巴特認為藝術(shù)來自相互凝視的語言,“意義或者意思不來自觀念,而來自某一種語言系統(tǒng)”;學(xué)者孫紹振提出了“錯位”理論,他認為藝術(shù)的感染力來自于審美價值與科學(xué)的認知、實用價值之間的“錯位”;英國評論家詹姆斯·伍德認為很多文學(xué)家寫出了偉大作品是因為他們制造出了“異化效果”,等等。
 (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從文本解讀到寫作實踐,“使對象陌生化”“相互凝視的語言”“錯位理論”“制造異化效果”……這樣一些闡釋小說如何成為一門藝術(shù)的理論得到有說服力的驗證。尤其是這些原理性的觀念和技法在寫作中的落實,最終促成了素材或事件向小說藝術(shù)的轉(zhuǎn)化。或者說,小說能成為一門獨立而美妙的藝術(shù),蓋因小說在完成的過程中遵循了藝術(shù)發(fā)生的本質(zhì)和策略,即以上提到的諸多藝術(shù)發(fā)生學(xué)理論。但作為后知后覺的藝術(shù)理論,有可能指導(dǎo)寫作,也有可能桎梏寫作,因為作品與理論之間總存在一個難以厘清的拉鋸戰(zhàn),有時作品在理論之前,有時理論在作品之前,有時二者并駕齊驅(qū),與作品的不斷誕生一樣,小說理論也在無限增殖和突破自我,所以關(guān)于小說的藝術(shù)理論永遠沒有盡頭和邊界。
藝術(shù)的魔力在于我們可以從諸多理論角度去靠近它,但永遠難以抵達它。因為小說藝術(shù)的永無完結(jié)性給了我們不斷從新的角度去靠近它的動力和可能。
鑒于此,當我們在經(jīng)典作品和時興作品之間徘徊許久,在小說的時代思潮和敘事風(fēng)向之間搖擺多時,尤其是,當我們面臨今日之自媒體時代,嚴肅小說藝術(shù)活力衰減和有效閱讀下降的雙重挑戰(zhàn)時,我們試圖生發(fā)出一些關(guān)于小說寫作的準理論或者觀念來,挽救小說藝術(shù)天空的一角,將小說藝術(shù)的水準維持在某種高級別狀態(tài)。照今日情形看來,我以為,小說由敘事或故事層面進入藝術(shù)層面,關(guān)鍵一點在于對日常生活和傳奇經(jīng)驗之間的一種平衡處理,小說藝術(shù)產(chǎn)生于日常與傳奇之間形成的張力,寫出日常生活的傳奇性或者寫出傳奇經(jīng)驗的日常性,并在這兩者之間達成平衡,藝術(shù)之境方可呈現(xiàn)。可以說,小說是這兩種敘事策略的平衡術(shù)。如果可能,我們將這種小說準理論稱為“平衡理論”。
小說的日常性和傳奇性并非新的說法,但又為何值得重新去思考它呢?一切蓋因自媒體時代對小說這一古老文體提出的新挑戰(zhàn)。
我們知道,自媒體時代最顯著的兩個特征是,信息生產(chǎn)量巨大(美國計算機工程師說近十年來的全球信息生產(chǎn)量等于人類三千年的信息量)和信息傳播速度快、獲取便捷(幾乎與信息生產(chǎn)同步)。面對鋪天蓋地而來的信息,讀者毫無抵抗力,甘愿或不甘愿地被裹挾甚至被“埋葬”,因為信息包含了吸引我們注意力的全部內(nèi)容,諸如經(jīng)驗、知識、故事、傳奇等。而小說從本質(zhì)上說也是一種信息的傳遞,只不過是小說家對信息(經(jīng)驗、故事等)藝術(shù)化、個人化處理之后以藝術(shù)作品之名進行的傳遞。那么,在時代與小說之間就出現(xiàn)了一個明顯的“信息落差”,當讀者在自媒體的無數(shù)信息中輕而易舉地就能得到精神啟蒙和精神滿足時,如果當前小說沒有超越這些信息的優(yōu)勢——足夠的敘事吸引力和精神震撼力,那么讀者勢必將會遠離當前小說,小說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活力也勢必隨之而衰。
加拿大傳播學(xué)者麥克盧漢曾提出人類傳播媒介發(fā)展的三個階段:口頭傳播時期,文字印刷傳播時期(即書籍報紙時代)和電子傳播時期(即電視時代)。在口頭傳播時代和書籍報紙時代,讀者和小說家之間幾乎不存在“信息落差”,甚至小說家的信息量大于讀者;而到了電視時代,這種“信息落差”出現(xiàn)了,但縫隙不大,所以本雅明感嘆“小說作為講故事這門古老的手藝衰落了”;在前兩個時代,一個聰明的小說家尚能彌補這種“信息落差”,但是如今,麥克盧漢沒有經(jīng)歷過的自媒體數(shù)字傳播時代,一個小說家如果不是足夠聰明或者偉大,他將很難填補這種“信息落差”。毫無疑問,信息的爆炸現(xiàn)場對小說寫作造成了重大挑戰(zhàn)甚至威脅,讀者的逃離是挑戰(zhàn)和威脅之一,而真正的挑戰(zhàn)和威脅來自小說家的無奈——“想象力已經(jīng)落后于極端的花哨現(xiàn)實”(喬治·斯坦納語)以及無法創(chuàng)造藝術(shù)的征服力去彌補“信息落差”。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當無數(shù)的光怪陸離的信息和現(xiàn)實奔涌到小說家面前時,是否為小說家打開了一扇巨大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素材之門呢?當然是。所以,找到處理信息(可供寫作的經(jīng)驗、素材或元故事)的原則和方式,將信息進行藝術(shù)的轉(zhuǎn)化成為關(guān)鍵。
二
在書籍、報紙盛行的時代,面對信息和經(jīng)驗的大量傳播,本雅明說:“無論何時,你只要掃一眼報紙,就會發(fā)現(xiàn)它(經(jīng)驗貶值)又創(chuàng)了新低。”“經(jīng)驗如此豐富,相反,值得講述的經(jīng)驗不是變得豐富而是變得貧乏了。”“值得講述”,一方面指讀者是否愛聽,另一方面指經(jīng)驗(信息)是否可以轉(zhuǎn)化為藝術(shù)作品。本雅明的意思并非否定和排斥信息和經(jīng)驗的豐富性,而是對小說家對經(jīng)驗的藝術(shù)處理和轉(zhuǎn)化能力提出了質(zhì)疑,他說“所有杰出的講故事的人的一個共同特征是,他們都能像在一架梯子上一樣在經(jīng)驗的梯子上自由地上下運動,梯子的一端伸入地下,一端直插云霄”,而今天講故事的人和“在經(jīng)驗的梯子上自由地上下運動”的能力都變得有所欠缺甚至有些衰弱。
英國評論家詹姆斯·伍德在談到一部小說的失敗情形時說:“我以為小說之失敗,不在于人物不夠生動或深刻,而在于該小說無力教會我們?nèi)绾稳ミm應(yīng)它的規(guī)則,無力就其本身的人物和現(xiàn)實為讀者營造一種饑餓。”這里有兩個關(guān)鍵詞:規(guī)則、饑餓。在詹姆斯·伍德看來,一部小說的寫作過程是制定一個自圓其說的故事規(guī)則和藝術(shù)規(guī)則的過程;其次,小說的敘述過程包括了教會或引導(dǎo)讀者去“適應(yīng)”這一規(guī)則,讓讀者進入這一“規(guī)則”的邏輯系統(tǒng)之中,此外,還包括營造一種閱讀饑餓感,即故事和人物的吸引力。無論規(guī)則的制定,還是饑餓感的營造,實際上是對信息(可供寫作的經(jīng)驗、素材或元故事)藝術(shù)化處理的過程。
從本雅明到詹姆斯·伍德,他們都發(fā)現(xiàn),無論從小說寫作的外部情形還是內(nèi)部情形來看,小說寫作即是藝術(shù)與信息之間的博弈。信息是肯定的,是疊加的,覆蓋式的,片斷式的,非敘事性;而小說是模糊的,獨立的,是思考的,敘事的,二者形成了某種對立。而且密集的信息不僅沒有解放想象力,相反壓制了想象力,想象力更多時候來自信息的匱乏,而想象力是小說藝術(shù)產(chǎn)生的原始動力。信息的豐富還導(dǎo)致了經(jīng)驗的同質(zhì)化,導(dǎo)致了敘事個性的消失。所以說,如何平衡信息與小說藝術(shù)之間的博弈,如何將信息(可供寫作的經(jīng)驗、素材或元故事)向小說藝術(shù)實現(xiàn)根本性的轉(zhuǎn)化,則成為一部小說是否成立的關(guān)鍵。
如果我們將信息分為日常生活和傳奇經(jīng)驗兩種——這種二分法基本涵蓋了所有信息——我們會發(fā)現(xiàn),小說藝術(shù)的呈現(xiàn)大致遵循了這樣一個原則或理論:如果我們寫的是一個日常生活故事,那么我們就得寫出它的傳奇性;如果我們寫的是一個傳奇經(jīng)驗或故事,那么我們就得寫出它的日常性。日常生活的傳奇性和傳奇經(jīng)驗的日常性,這二者的平衡處理,實質(zhì)上是在獨特、生動的“個”和普遍、寬闊的“類”之間展開,最終做到“個”中有“類”,“類”中有“個”,如黑格爾所說“藝術(shù)不應(yīng)該只以它的普遍性出現(xiàn),這普遍性必須經(jīng)過明晰的個性化,化成個別的感性東西”,小說的藝術(shù)性或藝術(shù)價值方才得以凸顯出來。
日出日落,黃昏到黎明,操持一日三餐,衣食住行,應(yīng)對生老病死;從家到超市,或趕往學(xué)校,或進入寫字樓,外出歸來,見面,寒暄,勞作,日復(fù)一日……這是日常生活最基礎(chǔ)的生存場景,真實,直接,平等。“日常生活是一種空間性的存在,卻展示了時間的內(nèi)涵”“它是一切,包圍著我們”“但像時間一樣,不知它從哪兒來,到哪兒去”——學(xué)者徐前進如是形而上概括。日常生活既無序又有序,既清晰又混沌,既瑣碎又整體,既有意義又無意義,它具備了匈牙利哲學(xué)家赫勒所說的惰性、實用主義目的、同質(zhì)性、排他性和自在性等特征,這一切注定了當我們把日常生活原封不動搬進小說時,因其無限重復(fù)、缺乏奇異、喪失意義感,它不僅摧毀讀者的閱讀耐心,也難以邁入藝術(shù)的層面。所以,要超越日常生活的重復(fù)、狹隘與功利,就必須將日常生活審美化、藝術(shù)化,即寫出它的傳奇性——賦予日常生活斷裂、驚奇和偉大。小說藝術(shù)也正是在日常生活(廣泛信息)這種傳奇性的轉(zhuǎn)化中完成的。
這種轉(zhuǎn)化的可能性并非空穴來風(fēng),而是有其理論根據(jù)。赫勒研究日常生活發(fā)現(xiàn),日常生活自身有兩種傾向:一是它作為一種“自在的”領(lǐng)域而存在;一是它是“自為的”領(lǐng)域的根基。前者構(gòu)成日常生活中現(xiàn)實的水平和狀態(tài),后者導(dǎo)向超越于日常生活本身。就是說,日常生活除了有自己“自在的”日常狀態(tài)之外,它還有一種超越自身的力量,它自身也在突圍自身,它自身也在尋找自己的傳奇,即那種被稱為“自為的”傳奇性。由此,我們可以說日常生活也具有“傳奇性”的根基和訴求,而小說家就是那個被選中的“傳奇性”的發(fā)現(xiàn)者和創(chuàng)造者。
美國小說家霍桑的短篇《威克菲爾德》堪稱把日常生活寫出傳奇性的經(jīng)典之作。威克菲爾德,一個極其普通的人,住在十九世紀倫敦一個普通的公寓里。一天早上,他告別妻子后離開了。他本來是出去幾天就回來,但他其實沒離開倫敦。他無緣無故,也沒有計劃,就租住在一間離家很近的房子里,一住就是二十年。“二十年來,他天天看見自己的家,也時常看到遭他遺棄的可憐而孤獨的太太。”忽一日,他晚上不聲不響踏進家門,仿佛才離家一天似的,從此成為溫存體貼的丈夫,直到去世。小說第一段就開門見山講述了這個驚人的傳奇,稱“威克菲爾德什么都沒做就留在了歷史上”,接下來的段落主要是回溯此人傳奇行徑的日常生活和日常遭際,為傳奇找到敘事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很顯然,如果霍桑只是不厭其煩地講述威克菲爾德出差幾天之后返回家里并與妻子天長日久的日常生活,那么這種重復(fù)、平淡、無意義感的日常敘事又有誰感興趣?也不會成為我們在150多年后討論的對象。正是這一傳奇性賦予了日常生活“價值”——意大利作家埃萊娜·費蘭特說:“威克菲爾德在場,同時又不在場……這種不動聲色的監(jiān)控,這種冷漠的接近,深深地吸引著我。”博爾赫斯說:“他在倫敦的中心,卻和世界失去了聯(lián)系。他沒有死,卻放棄了在活人中間的權(quán)利和地位。”——小說藝術(shù)也正是在日常生活的傳奇性轉(zhuǎn)換中得以成立。
如果說《威克菲爾德》的傳奇性具有一種極致性、力道偏大的話,那么韓東不久前發(fā)表的短篇《再婚》是另一條溫和的路子,日常生活中的傳奇性表現(xiàn)為細節(jié)的荒誕。母親四十八歲喪偶,直到六十歲時再婚嫁到了干部級別較高的好人崔伯伯家。兩位老人彼此傾心,相互照應(yīng),倒讓人安慰,但因崔家孩子摻和,母親在崔家的處境慢慢變化,由相安無事到冷戰(zhàn)紛爭再到動手,不久之后,母親離開崔家不再回去。這是一個典型的日常生活、家長里短的小說,讓這個小說脫胎為藝術(shù)的是一個頗具感染力的荒誕細節(jié):母親受到崔家兒子欺負后,“我”和哥哥發(fā)起“保衛(wèi)母親”的“戰(zhàn)役”,哥哥提出的掛牌示威引起媒體關(guān)注的方案被否定后,“我”每天去崔家陪伴母親以達到保衛(wèi)母親的目的。這一細節(jié)讓小說具有了一種愛——母子之愛和再婚老伴之愛——的酸楚,也正是這一荒誕細節(jié)讓小說具有了某種傳奇性,給日常生活敘事插上了藝術(shù)的翅膀,而具備精神的力量。
三
寫出日常生活的傳奇性是完成信息(經(jīng)驗、素材)到藝術(shù)轉(zhuǎn)換的途徑之一,反之,還有另外一條途徑是寫出傳奇故事的日常性。
學(xué)者吳曉東曾指出,20世紀之后,人類創(chuàng)造傳奇和講述傳奇的時代將終結(jié),他的理由是“現(xiàn)代生活世界的世俗化和庸常化,以及現(xiàn)代統(tǒng)治管理的日常化和體制化,使得人類那些毫無生趣和創(chuàng)造性的個體越來越陷于被約束被規(guī)范的境地”,傳奇因失去“超異的空間,超常的人物,超凡的舉動”等誕生土壤而終結(jié)。(見《20世紀最后的傳奇》)如今看來,吳曉東的判斷有失偏頗,21世紀人類個體的生機活力和創(chuàng)造力并沒有因為現(xiàn)代社會的庸常和體制而被約束被規(guī)范,相反,隨著自媒體時代的降臨,制造傳奇和講述傳奇如更大的旋風(fēng)一般席卷我們的世界。只要打開網(wǎng)絡(luò)熱搜或進入短視頻平臺,千奇百怪的信息和傳奇經(jīng)驗或故事層出不窮地冒出來,令人目不暇接,這些“極端的花哨現(xiàn)實”在各個數(shù)字終端被觀看、被消費,甚至被輕而易舉地添油加醋地“創(chuàng)作”之后再一次被傳播,數(shù)不盡的傳奇故事因此而誕生。制造、講述、消費傳奇在今日自媒體時代儼然已成為一樁全體網(wǎng)民參與的大生意,大受平臺和資本青睞。一則信息,其流量越大,收益越大,那么什么樣的信息流量會大呢?包含逸聞趣事、奇情怪人等的信息,那些情節(jié)離奇、人物行為不尋常的信息逐漸演化成傳奇經(jīng)驗或故事,無數(shù)讀者對之趨之若鶩。
事實上,自媒體時代為傳奇經(jīng)驗或故事的瘋狂生長提供了完備的技術(shù)和豐厚的營養(yǎng),再加上我們?nèi)祟惖奶煨灾杏兄圃靷髌婧椭v述傳奇的一面(毛姆將人類的這種天性看作是對平凡生活的浪漫抗議),一方面,對那些小概率發(fā)生、刺激性強烈的傳奇經(jīng)驗或故事我們毫無抵抗力,另一方面,我們?nèi)绱藷嶂躁P(guān)注傳奇是幻想有一天自己也成為傳奇。所以說,制造傳奇、講述傳奇永遠沒有終結(jié),傳奇無時無刻不在包圍著我們?nèi)粘G椰嵥榈纳睢?/p>
毫無疑問,這些傳奇信息或故事不僅對普通網(wǎng)民具有難以抗拒的吸引力,對小說家們也是如此,這是他們單調(diào)匱乏的日常生活和書齋經(jīng)驗之外寫作素材重要的來源和補充。但是,當小說家把目光投向這些傳奇經(jīng)驗或故事,借助想象力和虛構(gòu)把它們變成自己的小說時,我們看到了傳奇經(jīng)驗或故事轉(zhuǎn)換為小說的種種遺憾。有些小說只是傳奇經(jīng)驗或故事的擴展版,如啰嗦的新聞事件;有些小說描摹的人物大起大落,多寫的是時代熱門之事,如社會變革“大事記”;有些小說也試圖跳脫傳奇經(jīng)驗或故事的束縛,但因想象力和洞察力的欠缺,而成為藝術(shù)的半成品,等等。可以肯定,這類小說在藝術(shù)上是失敗的。對傳奇經(jīng)驗或故事的處理喪失了想象和虛構(gòu)的能力,導(dǎo)致了這類小說出現(xiàn)了一個新的敘事美學(xué)偏向,用張愛玲的話來說是:“許多作品里力的成份大于美的成份。”張愛玲認為:“好的作品,還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穩(wěn)做底子來描寫人生的飛揚的。沒有這底子,飛揚只能是浮沫,許多強有力的作品予人以興奮,不能予人以啟示,就是失敗在不知道把握這底子。”“力是快樂的,美卻是悲哀的,兩者不能獨立存在……它的刺激性大于啟發(fā)性。”自媒體時代遍地都是強有力的故事,我們的小說家大勢鋪染這種“力”,但“美”的成分減少,藝術(shù)終究從筆端溜走了。
如何從傳奇經(jīng)驗或故事的“力”中呈現(xiàn)出“美”來,有一策略:便是寫出它的日常性來,即寫出“飛揚”中的“安穩(wěn)”來。傳奇經(jīng)驗的“這一個”與日常性的“這一類”在小說中相遇的瞬間,藝術(shù)的化學(xué)反應(yīng)隨之發(fā)生,傳奇經(jīng)驗的“力”被普遍性的日常倫理削弱,而表現(xiàn)出小說的“美”來,諸如那種人類的普遍關(guān)切、情感以及認知等。美國當代小說家托馬斯·皮爾斯的短篇《總裁太空人》當是這一寫法的最佳說明書。
百萬富翁杜姆向教會捐獻了所有財產(chǎn)后,獲得了教會“上帝太空計劃”的一個艙位:移民另一個遙遠星球,去建立一個更加平等的社會,永不返回地球。杜姆和五百二十一個人將搭乘一艘二手飛船完成這次星際移民,在此之前,“上帝太空計劃”已經(jīng)發(fā)送了一艘載有十人先遣隊的飛船去這個星球。杜姆登上了這艘飛船,進入獨自的密封的冷凍柜后飛船起飛。蓋子打開了,杜姆在難以呼吸的冷凍柜中坐了起來,令他意外的是他返回了地球。工程師告訴他,在他們起飛十五年后,他們的飛船接到了先于他們到達的飛船的信號,另一種智慧生命已經(jīng)生活在那個星球上,它們不歡迎人類的出現(xiàn),這個信號自動重設(shè)了杜姆這艘飛船的返回計劃。杜姆返回時時間已經(jīng)過去了三十年,杜姆唯一的親人——他的前妻等著他。
這是一個融合了金錢、信仰和科幻元素的傳奇故事,很是奪人眼目,如果托馬斯·皮爾斯只是完成以上故事,感官上的確很精彩、很傳奇,但藝術(shù)上無可避免地流于平庸和乏味,但1982年出生的托馬斯·皮爾斯很聰明,他把這占全文三分之一的傳奇拆解于三分之二的日常敘事中,讓小說從“力”的敘事中轉(zhuǎn)移到了“美”的敘事中,小說由此轉(zhuǎn)向藝術(shù)的領(lǐng)地。他花大篇幅敘寫杜姆在永久離開地球的前一天的情形:他與他的前妻和解了,他為自己犯糊涂的一切表示后悔;他開車幾小時回去與父母擁抱,但不遇父母,他的父母在前幾天的告別會后已經(jīng)丟棄了他在地球上的成長物品,讓他感慨;他離開地球前的監(jiān)護人杰羅姆生活在困頓之中,杰羅姆的妻子企圖向這位百萬富翁討要一點錢,但杜姆說他現(xiàn)在只剩最后八十元了,杰羅姆的妻子拿走了這點錢……一個人要永久離開地球、離開親人時,一切便都有了特殊意義,有了值得珍惜和反思的價值。這些與我們每個人都有關(guān)的日常敘事讓杜姆的傳奇有了全新的藝術(shù)感染力和征服力。
所以說,寫出傳奇信息的日常性可以成為我們處理素材的有效策略之一。
對信息的兩種處理方式——無論是寫出日常生活的傳奇性還是寫出傳奇經(jīng)驗的日常性——實質(zhì)上都是小說藝術(shù)在建造一個信息領(lǐng)地的“他者”。面對日常生活的同質(zhì)化、重復(fù)性,藝術(shù)誕生于建造一個自我世界的“他者”;面對傳奇經(jīng)驗的奇崛性、獨一性,藝術(shù)誕生于建造一個眾我世界的“他者”。這個“他者”,顯現(xiàn)著平衡日常與傳奇之間所形成的張力,包括敘事的張力、思想的張力以及情感的張力等,張力即藝術(shù)。
其實,在寫出日常生活的傳奇性和寫出傳奇經(jīng)驗的日常性這兩種敘事策略的背后,隱藏著另一個同樣復(fù)雜難解的問題:何為小說藝術(shù)?托爾斯泰說“藝術(shù)是喚醒情感”;魯迅說藝術(shù)“是他的思想和人格的表現(xiàn)”;昆德拉認為小說藝術(shù)“是從幽默精神中產(chǎn)生的智慧”;弗洛伊德說“藝術(shù)引發(fā)了通曉自我的幻覺”等等。這些關(guān)于藝術(shù)的認識論雖林林總總,但殊途同歸,小說藝術(shù)山頂上有許多座山峰,通往藝術(shù)山峰的道路又有更多條,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對寫作而言,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通往小說藝術(shù)的道路是如何開辟的。
小說藝術(shù)之道,對讀者而言,是他們手中的一把鑰匙,用于開啟小說藝術(shù)之門;對小說作者而言,這些理論既成為認識論,也成為方法論。
關(guān)鍵詞:
 彩虹集團:公司線下營銷網(wǎng)絡(luò)覆蓋全國主要城市下沉到鄉(xiāng)鎮(zhèn),渠道穩(wěn)定 彩虹集團(003023)04月20日在投資者關(guān)系平臺上答復(fù)了投資者關(guān)心的問題。
彩虹集團:公司線下營銷網(wǎng)絡(luò)覆蓋全國主要城市下沉到鄉(xiāng)鎮(zhèn),渠道穩(wěn)定 彩虹集團(003023)04月20日在投資者關(guān)系平臺上答復(fù)了投資者關(guān)心的問題。
 豐網(wǎng)速運不斷優(yōu)化服務(wù),提升品質(zhì),助力電商用戶提質(zhì)增效 伴隨著電子商務(wù)的進一步發(fā)展,我國快遞行業(yè)也迎來了大踏步前進。數(shù)據(jù)顯示,2022年,全國
豐網(wǎng)速運不斷優(yōu)化服務(wù),提升品質(zhì),助力電商用戶提質(zhì)增效 伴隨著電子商務(wù)的進一步發(fā)展,我國快遞行業(yè)也迎來了大踏步前進。數(shù)據(jù)顯示,2022年,全國  a2至初奶粉好不好:好消化吸收的奶粉還得看TA 每一代的中國媽媽們都有著自己的育兒經(jīng)驗,對于崇尚科學(xué)育兒的新生代父母來說,他們更
a2至初奶粉好不好:好消化吸收的奶粉還得看TA 每一代的中國媽媽們都有著自己的育兒經(jīng)驗,對于崇尚科學(xué)育兒的新生代父母來說,他們更  爆炸蒸汽深度軟化褶皺,米家手持蒸汽熨燙機全新上線! 你穿什么,你就是什么。人都是視覺動物,任何人遇見不熟悉人的時候,都是通過對方的外
爆炸蒸汽深度軟化褶皺,米家手持蒸汽熨燙機全新上線! 你穿什么,你就是什么。人都是視覺動物,任何人遇見不熟悉人的時候,都是通過對方的外  出彩每一面,吸睛全場面!艾瑞澤8&楊紫聯(lián)名紫色車型閃耀上海車展 4月18日,2023年上海國際車展盛大開幕,奇瑞以科技·有愛為參展主題,攜旗下四大品牌
出彩每一面,吸睛全場面!艾瑞澤8&楊紫聯(lián)名紫色車型閃耀上海車展 4月18日,2023年上海國際車展盛大開幕,奇瑞以科技·有愛為參展主題,攜旗下四大品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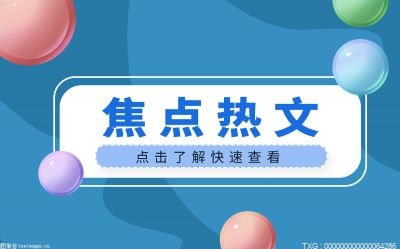 一招短線選股法是什么意思?尾盤買入法的好處有哪些?拉尾盤什么意思? 尾盤買入法:屬于短線的操作,今天買了,明天就有機會賣的。每天下午14:30分的時候有
一招短線選股法是什么意思?尾盤買入法的好處有哪些?拉尾盤什么意思? 尾盤買入法:屬于短線的操作,今天買了,明天就有機會賣的。每天下午14:30分的時候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