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山西大同華嚴寺大雄寶殿是一座遼代建筑。為有效保護古建筑,以大雄寶殿為例,采用現場調查與分析論證結合的手段,研究了遼代建筑的抗震構造。結果表明:大雄寶殿浮放石柱礎、榫卯、鋪作等構造可發揮耗能減震功能,立柱、梁架、建筑高寬比有利于結構抗震穩定;但減柱造形式使得建筑易于產生扭轉,高臺使得上部結構所產生的地震響應放大。
 【資料圖】
【資料圖】
關鍵詞:華嚴寺大雄寶殿;古建筑;木結構;抗震構造;構造缺陷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華嚴寺內的大雄寶殿,建于金天眷三年至皇統四年(1140-1145),為我國現存遼金建筑中較大的佛殿。大雄寶殿坐落于高臺之上(圖1),坐西向東,面寬9間、進深5間,建筑平面尺寸為53.7×27.5m(長×寬),采用了“減柱造”的柱網形式。建筑高度17.4m(室內地面到正脊正中上皮),正脊兩端還有高達4.5m的鴟吻。建筑屬木結構承重構架,梁架形式為中央7間前后三椽栿用四柱,左右盡間前后乳栿用六柱,單檐廡殿屋頂。殿身四壁不設窗戶,僅在前檐明間及左右稍間隔開設壺門一道。殿內有明代塑像32尊,四面墻壁繪有大量的清代壁畫。無論是建筑本體,還是建筑內的雕塑與壁畫,均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
圖1 大雄寶殿外立面
Fig.1 Front view of Daxiong Palace
大同是地震多發區。據統計,自公元512年以來,大同地區共遭受7度以上的地震破壞11次,因而是山西省防震重點區域[1]。近年來,我國地震活動頻繁,對古建筑安全造成了嚴重威脅。部分學者開展了古建筑的抗震性能相關研究,近期主要成果有:陳志勇等(2013)[2]評價了應縣木塔(遼)在不同強度地震作用下的抗傾覆性能;淳慶等(2018)[3]研究了故宮靈沼軒(清)的抗震性能;周乾等(2020)[4-5]討論了明清官式古建抗震構造,評價了結構整體抗震性能;薛建陽等(2021)[6]基于屋蓋質量、木材順紋彈性模量參數,討論了新城開善寺大殿(遼)抗震性能等。然而對于華嚴寺大雄寶殿而言,抗震相關研究,尤其是抗震構造的系統化研究,則相對較少。本研究基于已有成果,討論該建筑的不同構造如基礎、立柱、榫卯節點、鋪作、梁架等,對結構整體抗震的有利影響;分析平面布局、高臺構造對建筑抗震的不利影響,為遼金建筑的修繕保護提供理論參考。
1 抗震構造
1.1柱礎
大雄寶殿的柱徑約為0.7m,而柱頂石邊長在1.20-1.34m之間,基本上符合宋《營造法式》卷三規定的“造柱礎之制,其方倍柱之徑”的規定。大雄寶殿在2001年大修時拆下的檐柱柱根照片資料見圖2(a),易知柱根底部平整且完好(無糟朽或埋入地下的痕跡),不難推測出柱根是浮放立于柱頂石之上。圖2(b)為清代柱頂石照片資料,易知其頂面平整,利于立柱浮放,且可為大雄寶殿柱頂石構造特征提供參考。而從抗震角度講,柱根與柱頂石之間的“平擺浮擱”關系,有利于柱底在柱頂石表面往復運動,并產生摩擦耗能的性能[7];柱頂石邊界與柱根邊界有一定的距離,可減小柱根從柱頂石滑落的風險[8]。
(a) 大雄寶殿檐柱柱根
(b) 柱頂石
圖2 柱根與柱頂石的照片
Fig.2 Photos of column root and stone base
作者曾開展了地震作用下單檐歇山屋頂類古建筑模型的振動臺試驗,獲得了柱底平擺浮擱于柱頂石條件下,柱架的運動特性與減震性能[5,9]。地震作用下,柱架產生搖晃,而柱根則在柱頂石上滑動。地震波作用結束后,柱根與柱頂石產生了一定的摩擦滑移距離。從試驗現象來看,柱架的運動猶如站立的人,其兩腳八字形邁開,左、右腳分別抬起—落地的反復運動,并伴隨著柱腳與柱頂石之間往復摩擦滑移的運動狀態。由于柱架上部屋頂重量較大,產生了較大的恢復彎矩,使得地震結束后,柱腳能恢復到原有位置附近,且不脫落于柱頂石。另由試驗數據分析可知,當地震波傳至柱底位置時,由于柱底與柱頂石之間的摩擦運動,耗散部分地震能量,使得該位置加速度峰值略有降低。由上述分析不難推測出,大雄寶殿柱與柱礎之間的摩擦滑移及搖擺運動亦能發揮耗能減震作用。
1.2立柱
1.2.1 生起與側腳
“生起”屬于宋式古建大木作術語,主要是指古建筑在立面上,柱高尺寸不一,從明間檐柱開始,向兩側逐漸增加[10]。《營造法式》卷五《大木作制度二·柱》規定了生起的具體做法[11]:“凡用柱之制,……至角則隨間數生起角柱”;“若十三間殿堂,則角柱比平柱生高一尺二寸;十一間生高一尺;九間生高八寸;七間生高六寸;五間生高四寸;三間生高二寸”。大雄寶殿面寬九間,按照《營造法式》規定,其生起的總尺寸為8寸,約為0.26m(考慮1寸≈0.32m)。而大雄寶殿明間檐柱高6.98m,角柱高7.30m,生起尺寸大于《營造法式》的規定值。大雄寶殿生起構造做法可由圖3表示。生起不僅可使建筑外立面產生優美的曲線弧度效果,還使得建筑整體呈現“凹”字形,重心降低,因而可減小地震作用下建筑物的搖晃幅度。此外,生起構造使得立柱與額枋并非垂直搭接,而是處于略微傾斜狀態,有利于榫頭與卯口的擠緊,增強其相對轉動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提高節點的耗能性能,且榫卯節點還可提供部分水平分力,以抵抗水平地震作用[12-13]。
圖3 大雄寶殿的側腳與生起
Fig.3 Cejiao and Shengqi constitution of Daxiong Palace
側腳屬于宋、清木構古建筑的構造做法,即建筑外檐立柱柱根向外“掰”出一定尺寸。營造法式》卷五《大木作制度二·柱》規定[11]:“凡立柱,并令柱首微收向內,柱腳微出向外,謂之側腳。每屋正面……每一尺,即側腳一分;若側面……每長一尺,側腳八厘”,即規定了檐柱的側腳尺寸為柱高的(0.8-1)%。大雄寶殿屬于金代建筑,其側腳平均尺寸約為0.17m,是檐柱柱高的2.4%,遠大于《營造法式》的規定值。這種構造是有利于結構抗震的。側腳使得柱架由近似長方形,變成了有虛交點的三角形,見圖4(a)所示,而后者在地震作用下的穩定性明顯強于前者。另古建筑震害及試驗研究表明[9,14]:立柱側腳使得結構整體重心降低;地震作用下,結構以柱腳為支點,不斷做往復搖晃運動,并能恢復到原始位置附近,猶如不倒翁一般,見圖4(b);側腳的構造,使得立柱與額枋的榫卯連接即使受到破壞,也不會引起柱架的局部失穩。因此,側腳構造有利于結構的抗震。
(a) 側腳
(b) 柱架運動
圖4 側腳減震示意圖
Fig.4 Sketches of aseismic performance of Cejiao
1.2.2 卷殺
大雄寶殿的柱子有卷殺做法,其特點是:在柱上部至柱頂高度范圍內,柱截面尺寸逐漸縮小,使得柱身上部的兩側呈現略向內的彎曲狀。《營造法式》卷五《大木作制度二·柱》對柱子的卷殺做法有明確的規定[11]:“凡殺梭柱之法,隨柱之長,分為三分,上一分又分為三分……又量柱頭四分,緊殺如覆盆樣,令柱項與櫨枓底相副”,即對于立柱而言,沿柱高將其分為三等分,而最上面的部分再分為三等分,在柱頂位置做四分的卷殺(圖5)。由于殿堂型建筑立柱直徑一般為45分(三材,一材為15分,“分”同“份”),不難推測出卷殺尺寸為柱徑的4/45。從構造上講,大雄寶殿柱頂之上為普拍枋,普拍枋截面寬度與櫨斗底部寬度近似相同。實測大雄寶殿的柱底直徑約為0.68m,柱頂卷殺尺寸約為0.05m,該尺寸與《營造法式》規定相近。
圖5 柱卷殺示意圖
Fig.5 Sketch of curve shape of column top
卷殺做法不僅使得立柱有著優美的外形,而且有利于其在地震作用下保持穩定狀態。當柱頂截面尺寸減小到與上部普拍枋截面寬度相近時,有利于斗拱(鋪作層)傳來的豎向力與柱身中心線在方向上重合,減小立柱受到的偏心彎矩,并減小水平地震力作用下立柱與上部構件之間的相對搖晃[15]。不僅如此,卷殺構造使得立柱的立面邊線形成三角形虛交點的穩定構造,且重心降低,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減小水平地震力繞柱底產生的傾覆彎矩。
1.3 榫卯
大雄寶殿為木結構,其典型構造特征之一即立柱與梁、枋采用榫卯連接。其具體做法為:梁、枋水平構件的端部做成榫頭形式,插入立柱頂部預留的卯口中。《營造法式》卷三十的圖樣中,展示了幾種典型的宋代榫卯節點樣式,其中梁柱連接的形式有“攝口鼓卯”(圖6上)、“鼓卯”(圖6中)、梁柱對卯“藕批搭掌,蕭眼穿串”(圖6下)等。此處“鼓卯”是指燕尾榫,“藕批搭掌”即搭掌榫(猶如巴掌相合的連接方式),“蕭眼穿串”即用木梢穿過搭掌榫上預留的卯口。
圖6 《營造法式》中的梁柱榫卯節點示意圖
Fig.6 Sketch of tenon-mortise joints in Ying-Tao-Fa-Shih
大雄寶殿的榫卯節點有多種,歸納起來可分為燕尾榫和直榫兩種節點形式[16],見圖7。燕尾榫端部寬、根部窄,與之相應的卯口是里面大、外面小,一般通過上起下落的方式進行安裝,一般用于拉扯聯系構件,如椽栿、普拍枋、闌額等水平構件與垂直構件相交部位;安裝后的燕尾榫由于受到卯口約束,因而在地震作用下不易拔榫;直榫形狀特點是榫頭端部和根部一樣寬,主要用于需要拉接,但無法用上起下落方法安裝的部位,如乳栿兩端、剳牽與內柱相交處、叉手與蜀柱相交處等;安裝后的直榫在地震作用下容易拔榫,但由于榫頭長度充足,因而不會出現脫榫[17]。
(a) 燕尾榫
(b) 直榫
圖7 典型榫卯節點示意圖
Fig.7 Sketches of typical tenon-mortise joints
理論和試驗研究表明[13,18-19]:地震作用下,榫頭與卯口之間可產生相對擠壓和轉動,并可耗散一定的地震能量,猶如在節點位置安裝了阻尼器。其耗能的主要特點為[18]:在地震力作用的初期階段,榫頭與卯口之間的相對擠壓和轉動能力較強,耗散能量較大;隨著地震力持續作用,榫頭出現拔榫(非脫榫),榫卯與卯口之間的轉動能力有所減弱,但是仍可發揮較好的耗能能力,并保持較為穩定的耗能狀態。榫卯節點的耗能特性與其節點特征密切相關[20]:榫頭與卯口之間的連接屬于半剛性連接(介于鉸接和剛接之間的連接),這使得榫頭與卯口之間存在一定的轉動能力,可傳遞部分彎矩;從結構振動角度而言,半剛性節點與彈簧的剛度特性有相似之處,因而可減小結構整體剛度,增大建筑自振周期,對建筑產生隔震性能有一定的積極貢獻。另有研究表明[19,21]:與梁柱采用剛接節點形式相比,榫卯節點連接方式可有效地減小結構在不同方向的加速度響應峰值,且在水平方向的加速度峰值可降至剛接節點條件下的68.5%;而與古建筑其他抗震構造如浮放柱礎、斗拱、墻體、斗拱等相比,榫卯節點的耗能性能最佳。
1.4 鋪作
大雄寶殿的鋪作層位于普拍枋之上,可包括柱頭、轉角、補間(立柱之間)三種。除了稱謂不同外,大雄寶殿的鋪作在構造與功能方面與清代斗拱高度相近。大雄寶殿鋪作從櫨斗到撩檐槫總高度為1.62m,約為檐柱高度的1/4.3。其補間鋪作華拱兩側各出一層45度的斜拱,體現了遼代建筑的特色。建筑鋪作用材較為規整,拱材斷面寬度一般為0.2m,高寬比為3:2,材栔比為6.5:15。以稍間的補間鋪作為例(圖8),來說明大雄寶殿的鋪作構造特點。該鋪作屬于五鋪作雙抄重栱(拱)造,由下往上的分層組成為:柱頭枋以外部分,櫨斗之上,有泥道栱,并向外出華拱二跳,第一跳上有瓜子拱、慢拱、羅漢枋,瓜子拱兩端之上又出挑45度斜拱一層,斜拱上部支撐隨槫枋;柱頭枋以內部分,向外出挑五跳,第一、二跳為計心造做法,有瓜子拱、慢拱、羅漢枋,且第一跳瓜子拱上方有45度斜拱,第三至五跳為偷心造做法。
(a) 外立面照片
(b) 橫剖面
圖8 大雄寶殿稍間鋪作
Fig.8 Bracket sets of the Shaojian part of Daxiong Palace
1.4.1 彈性恢復
在靜止狀態下,大雄寶殿鋪作底部的櫨斗通過暗銷與普拍枋(類似于圈梁功能)相連接,普拍枋浮放在柱頂之上,櫨斗上部的荷載N通過櫨斗中心作用于柱頂。發生地震時,立柱繞底部支點O產生搖晃,并與普拍枋形成一定的夾角。在普拍枋保持近似水平的條件下,櫨斗傳來的豎向荷載變為N’,且通過普拍枋與柱頂的交點O’傳至柱頂。N’與OO’的間距D’的乘積N’’形成抵抗彎矩,可抵抗柱頂水平地震力F’繞O點產生的傾覆彎矩F’H’(圖9)。對于立柱而言,表現為以柱底兩端為支點的往復搖擺—復位運動。這種彈性恢復運動可稱為“高位不倒翁”現象。
圖9 鋪作的彈性恢復作用
Fig.9 Elastic restoration of the bracket sets
1.4.2 水平耗能
大雄寶殿鋪作的水平耗能性能主要通過構件之間的摩擦、擠壓和錯動產生。作者曾開展故宮太和殿斗拱的水平抗震性能試驗,獲得了清式斗拱的水平耗能機理[22-23]:水平地震作用下,斗拱不同構件之間產生擠壓和錯動,使得斗拱表現為較為明顯的滑移特性,并表現為一定的減震性能。基于坐斗(相當于“櫨斗”)受到往復荷載作用,產生運動,帶動下部的正心瓜拱(“泥道拱”)和翹(“華拱”)產生運動,并與其產生相對擠壓和摩擦作用,斗拱產生耗能;隨著坐斗受荷增大,產生側移增大,并帶動下部各層的拱、枋、昂逐漸產生沿荷載作用方向的不同程度運動,且在運動過程中彼此擠壓、摩擦,其耗能作用趨于明顯;當斗拱側移值進一步增大時,由于外力增大,斗拱構件間產生變形、破壞、較大空隙等問題,因而耗能能力相對降低。由于大雄寶殿鋪作構造與太和殿斗拱構造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不難推斷出:大雄寶殿的鋪作層在水平方向上具有一定的耗能能力。
1.4.3 豎向減震
大雄寶殿的鋪作層在豎向是由若干層木構件疊加而成的。由于木材的彈性模量遠小于砌體、混凝土或鋼材材料,因而鋪作在豎向的構造猶如若干彈簧串聯[24-25]。地震作用下,鋪作構件在豎向的彈性變形可把部分地震能量轉化為重力勢能,產生一定的隔震效果,其隔震率可表示為[26]:
式(1)中,TR為傳導比,TR值越小,則鋪作的隔震效果越好;ω、ωn分別為地震波、屋頂(位于鋪作層之上)的圓頻率;ξ為屋頂阻尼比。研究表明[27]:當ω/ωn>21/2時,此時恒有TR
1.5 梁架
梁架位于斗拱(鋪作層)之上、屋檐之下,主要用于承擔屋頂的重量,并傳給斗拱。大雄寶殿的梁架下部用三椽乳栿拉接節檐柱與金柱,使之協調受力;上部為核心部分,分別由六椽栿、四椽栿、平梁從下往上層層“抬”起,最上層為蜀柱,且兩端有叉手固定,使得梁架整體形成近似三角形狀的受力體系,而上下層的梁栿之間,則通過駝峰或長方形拱材支撐(圖10)。在常遇地震作用下,梁架核心部分的防傾覆、防滑移構造是抗震構造評估的重要內容,以下予以分析。
圖10 大雄寶殿明間梁架示意圖(單位:mm)
Fig.10 Sketch of beam system of Mingjian part of Daxiong Palace (Units: mm)
1.5.1 抗傾覆
大雄寶殿梁架核心部分的計算簡圖可由圖11表示。其中,L1表示六椽栿兩端支點的間距,L1=16.82m;H1表示六椽栿形心至梁架頂部的距離,近似取值H1=5.89m;FEK為水平地震力標準值;G1為六椽栿及上部屋頂重量;FS為六椽栿底部與斗拱頂部靜摩擦力。
圖11 梁架計算簡圖
Fig.11 Calculation diagram of the beam system
水平地震作用下,如梁架不產生傾覆,則地震力產生的傾覆彎矩,不超過梁架及上部屋頂重量產生的抵抗彎矩。假設梁架重心在其高度的1/3位置,則水平地震力作用下,梁架不發生傾覆的條件應滿足(2)式。
FEK×H1/3≤G1×L1/2 (2)
參照《建筑抗震設計規范》(GB50011-2010)(以下簡稱為《規范》)第5.2.1條規定,FEK可用(3)式表示,其中,Geq為結構等效質量,此處Geq=G1;α為相應于結構基本自振周期的水平地震影響系數,大雄寶殿所在地區為7度抗震設防,設計基本地震加速度為0.15g(g為重力加速度),設計地震分組為第一組,查詢《規范》5.1.4條對應的表格,可取最大值,α=0.12(常遇地震)。
FEK=Geq×α (3)
將(3)式代入(2)式,可得(2)式左邊值為0.71G,右邊值為8.41G,即大雄寶殿梁架滿足7度常遇地震作用下的抗傾覆構造要求。
1.5.2 抗滑移
如不考慮六椽栿底部與斗拱頂部之間的暗銷連接,則7度常遇水平地震作用下,梁架不產生水平錯動的基本條件為:水平地震力不超過梁架與斗拱頂之間的靜摩擦力,見(4)式。其中,μ1為木構件之間的靜摩擦系數,基于試驗結果[28],可取值μ1=0.33。
FEK≤FS=G1×μ1 (4)
將(3)式代入(4)式,可得(3)式左邊值為0.12G1,右邊值為0.33G1,即大雄寶殿梁架滿足7度常遇地震作用下的防滑移構造要求。
1.6 高寬比
大雄寶殿的建筑高寬比符合《營造法式》的規定,且有利于抵抗地震力產生的傾覆彎矩。大雄寶殿明間橫剖面見圖12。《營造法式》卷五“大木作制度二”規定:“凡用柱之制……下檐柱雖長,不越間之廣”[11],意即外檐檐柱的高度不得超過構架的進深寬度。以下從抗震角度來說明這種規定的合理性。將上述木構架簡化為圖13所示的受力體系。其中,屋頂用質量為M的塊體表示,建筑的寬度為L、外檐柱高度為H,水平地震力為F,g為重力加速度,柱底與柱頂石之間的靜摩擦系數為μ。則在水平地震作用下,屋頂不產生傾覆的基本條件為:地震力產生繞柱腳產生的傾覆彎矩,不超過屋頂質量繞柱腳產生的抵抗彎矩,即:
FH=MgμH≤MgL/2(5)
圖12 大雄寶殿明間橫剖面(單位:mm)
Fig.12 Section view of Mingjian part of Daxiong Palace (Units: mm)
圖13 柱架計算簡圖
Fig.13 Calculation diagram of the column structure
取值μ=0.5[29],則(5)式可得:H≤L,與“不越間之廣”相符。圖12所示的大雄寶殿明間檐柱高6.98m,而建筑的進深尺寸為27.40m,滿足《營造法式》的規定。
2 抗震缺陷
2.1 平面
大雄寶殿的平面示意圖見圖14(a),易知大雄寶殿是面寬9間、進深5間的平面布局形式,但是做了“減柱造”處理。這種平面處理形式為遼金元時期建筑的主要特點,即為了開展聚集性活動需要,大雄寶殿從明間到左右兩側的稍減(共7開間)進行了減柱處理,進深柱網由5間縮減為3間,共減少立柱12根。需要說明的是,在古建筑領域,開間即縱向的柱距,進深是指橫向的柱距。作為對比,北京故宮太和殿平面柱網亦為面寬9間、進深5間,但未作減柱造處理,立柱無論在在橫向還是縱向,均為均勻對稱的布局方式,見圖14(b)。太和殿平面布局方式的抗震優勢在于[27,30]:布局均勻、對稱,有利于使得結構的質心與抵抗水平地震力的抗力剛度重合,減小結構在地震作用下產生扭力等不利內力;結構振動形式主要以縱向或橫向的平動為主,且結構在兩個方向的振動沒有關聯,在地震作用下不易因扭轉而產生受力破壞。而大雄寶殿采用減柱造做法后,由于其中部區域立柱數量減少,因而很難保證結構的質心與抵抗水平地震力的抗力重合,且在地震作用下很可能產生扭轉等不利結構安全。另有研究表明[31]:“減柱造”做法,使得結構剛度不均,結構主振型有較為明顯的扭轉特性,地震作用下結構變形不協調,穩定性降低。因此,大雄寶殿的“減柱造”平面柱網形式不利于抗震。
(a) 大雄寶殿
(b) 太和殿
圖14 大雄寶殿與太和殿平面對比(單位:mm)
Fig.14 Plan view of Daxiong Palace against Taihe Palace (Units:mm)
2.2 高臺
遼金時期的佛寺主殿多以高聳的臺基進行烘托,而大雄寶殿建立在高達4m的高臺之上。高臺是由多層土堆疊而成的臺基。古代重要的建筑多建造于高臺之上,不僅可展現建筑高大雄偉、莊嚴尊貴的視覺效果,還有利建筑使用者登高望遠、擴大視野,且有利于木結構建筑的防潮與通風。大雄寶殿高臺的臺面長61.4m、寬34.3m。臺基側幫下部為青磚砌筑,磚層上面是石質階條石和欄板。臺基地面為約0.45m厚的石材面層,石面層以下為分層填充材料夯實,主要材料包括素土、碎石、磚、瓦、動物骨骼等[32]。臺基地面以上為柱頂石。柱頂石為立柱基礎,其上部表面平整(無管腳榫做法),尺寸多為1.17×1.14×0.40m(長×寬×高)。柱頂石與高臺頂面的連接材料為1.2×1.17×0.35m(長×寬×高)的砂層[32]。
高臺對上部結構抗震性能的影響不可忽視。作者開展了太和殿基座(高8.13m)對太和殿建筑本體的抗震性能影響,發現由于高臺的作用,使得太和殿結構的自振特性變化,使得結構基頻減小,主振型參與系數增大;地震作用下,高臺使得太和殿墻體所受內力峰值縮小,變形及加速度響應峰值則有不同程度的放大,其主要原因在于基座參與了結構振動,并使得結構整體剛度變小[33]。另高臺屬于生土結構,有研究表明[34]:生土結構自重大、延性較差,地震作用下容易產生破壞,且生土高臺的上部結構,在水平地震作用下,容易在頂部產生放大效應,形成較大的傾覆彎矩,不利于上部結構抗震。而2008年汶川地震中,建造在高臺基之上的青城山上清宮門樓出現了臺基錯動、屋面椽子、室內頂棚脫落、榫卯節點拔榫等震害,其主要原因即為臺基與門樓之間的連接強度較差、剛度突變導致的鞭梢效應[35]。由上可知,大雄寶殿的高臺構造,對上部結構的抗震性能有不利影響。
3 結論
華嚴寺大雄寶殿的不同構造,對結構整體抗震性能影響如下:
(1)柱與柱礎之間的摩擦滑移及搖擺運動,可產生耗能減震的效果;
(2)柱的側腳、生起與卷殺構造,有利于提高結構整體的抗震穩定性能;
(3)榫頭與卯口之間的相對擠壓和轉動,可耗散部分地震能量;
(4)鋪作層在地震作用下,可產生“高位不倒翁”現象,且構件之間的摩擦、擠壓和錯動,可產生水平耗能與豎向減震效果;
(5)梁架低矮,在設防烈度地震作用下,可滿足抗傾覆、抗滑移要求;
(6)建筑高寬比較小,有利于抵抗地震力產生的傾覆彎矩。
(7)平面“減柱造”做法,使得結構剛度不均,地震作用下很易扭轉,不利于抗震。
(8)高臺使得地震作用下,上部結構的變形及加速度響應放大,不利于抗震。
參考文獻
[1]孫國學.山西地震災害損失預測及減災對策的初步研究[J].山西地震,1992,(S1):1-96
[2]陳志勇,祝恩淳,潘景龍.應縣木塔精細化建模及水平受力性能分析[J].建筑結構學報,2013,34(9):150-158
[3]淳慶,張劍葳,趙鵬,等.故宮靈沼軒的動力特性及抗震性能研究[J].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018,30(2):54-62
[4]周乾,閆維明,楊娜.紫禁城古建木柱抗震穩定構造[J].工程抗震與加固改造,2020,42(3):149-156
[5]周乾,閆維明,楊娜,等.單檐歇山式木構古建抵抗極端烈度地震試驗調查研究[J].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020,32(2):29-44
[6]薛建陽,吳晨偉,張雨森.殿堂式木結構古建筑屋蓋梁架體系動力特性及地震響應分析[J].建筑結構學報,2021,42(10):87-95
[7]姚侃,趙鴻鐵.木構古建筑柱與柱礎的摩擦滑移隔震機理研究[J].工程力學,2006,23(8):127-131
[8]周乾,閆維明,關宏志,等.罕遇地震作用下故宮太和殿抗震性能研究[J].建筑結構學報,2014,35(S1):25-32
[9]周乾,閆維明,紀金豹,等.單檐歇山式古建筑抗震性能振動臺試驗[J].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018,30(2):37-52
[10]王效青.中國古建筑術語辭典[M].太原: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113
[11]王海燕.《營造法式》譯解[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1
[12]姚侃,趙鴻鐵,薛建陽,等.古建筑木構架的整體穩定性分析[J].世界地震工程. 2008,24(1):73-76
[13]周乾,楊娜.《營造法式》構造的力學意義研究[J].水利與建筑工程學報,2018,16(2):11-18
[14]周乾,閆維明,楊小森,等.汶川地震古建筑震害研究[J].北京工業大學學報,2009,35(3):330-337
[15]吳玉敏,張景堂,陳祖坪.殿堂型建筑木構架體系的構造方法與抗震機理[J].古建園林技術, 1996,(04):32-36
[16]馬炳堅.中國古建筑木作營造技術[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1
[17]周乾,閆維明,紀金豹.木構古建梁柱節點拔榫過程數值仿真[J].山東建筑大學學報,2014,29(4):308-314
[18]周乾,閆維明,周錫元,等.古建筑榫卯節點抗震性能試驗[J].振動、測試與診斷,2011,31(6):679-684
[19]周乾,閆維明,周錫元,等.中國古建筑動力特性及地震反應[J].北京工業大學學報,2010,36(1):13-17
[20]張雷,楊娜.均布荷載作用下榫卯連接木梁的解析解[J].工程力學,2017,34(07):51-60
[21]周乾,閆維明,關宏志,等.故宮太和殿減震構造分析[J].福州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3,41(4):652-657
[22]周乾,楊娜,閆維明,等.故宮太和殿一層斗拱水平抗震性能試驗[J].土木工程學報,2016,49(10):18-31
[23]周乾,楊娜,淳慶.故宮太和殿二層斗拱水平抗震性能試驗[J].東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7,41(1):150-158
[24]周乾,閆維明,慕晨曦,等.故宮太和殿一層斗拱豎向加載試驗[J].西南交通大學學報,2015,50(5):879-885
[25]周乾,閆維明,慕晨曦,等.故宮太和殿二層斗拱豎向加載試驗[J].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017,29(2):8-14
[26]劉晶波,杜修力.結構動力學[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5:56-57.
[27]周乾,閆維明,紀金豹.故宮太和殿抗震構造研究[J].土木工程學報,2013,46(S1):117-122
[28]王其超.滑動摩擦系數的測定[J].教學儀器與試驗,1987,3(2):15-16
[29]張鵬程.中國古代木構建筑結構及其抗震發展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學,2003:47-48
[30]周乾,閆維明,關宏志,等.故宮太和殿動力特性與常遇地震響應[J].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015,27(1):46-52
[31]童麗萍,蔣浩,劉應揚,等.會善寺大雄寶殿結構動力性能分析[J].世界地震工程,2019,35(1):220-227
[32]齊平,柴澤俊,張武安,等.大同華嚴寺(上寺)[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33]周乾,楊娜,閆維明.太和殿基座對上部結構抗震性能影響分析[J].地震工程學報,2017,39(6):981-995
[34]潘毅,謝丹,袁雙,等.尼泊爾8.1級地震文化遺產建筑震害調查與分析[J].西南交通大學學報,2015,50(6):1-8
[35]余志祥,趙世春,潘毅,等.青城山上清宮門樓古建筑震害機理分析與研究[J].四川大學學報(工程科學版),2010,42(5):292-296
(《工程抗震與加固改造》2023年第1期刊載)
關鍵詞:
 蘋果公司開始對合同工進行裁員?據知情人士透露:公司已悄悄開始削減合同工數量 【 蘋果公司開始對合同工進行裁員 】 財聯社2月17日電,到目前為止,蘋果避免了亞
蘋果公司開始對合同工進行裁員?據知情人士透露:公司已悄悄開始削減合同工數量 【 蘋果公司開始對合同工進行裁員 】 財聯社2月17日電,到目前為止,蘋果避免了亞
 19元入手一款FENDI聯名產品,能解喜茶的困境嗎?|每日簡訊 此次喜茶與FENDI聯名效果不凡,但此次活動為限時活動,聯名給喜茶帶來的加成效應會隨
19元入手一款FENDI聯名產品,能解喜茶的困境嗎?|每日簡訊 此次喜茶與FENDI聯名效果不凡,但此次活動為限時活動,聯名給喜茶帶來的加成效應會隨
 前海人壽分享:重疾險和醫療險的區別;教師周冬梅:為教育奉獻青春與力量 前海人壽:重疾險與醫療存在三個方面的區別重疾險和醫療險有什么區別?重疾險與醫療險在
前海人壽分享:重疾險和醫療險的區別;教師周冬梅:為教育奉獻青春與力量 前海人壽:重疾險與醫療存在三個方面的區別重疾險和醫療險有什么區別?重疾險與醫療險在  禪意安和,柔護身心——愛慕全新禪柔IV運動系列 瑜伽這種古老的身心練習方式,結合呼吸控制、身體控制和冥想來促進身心的健康和平衡,
禪意安和,柔護身心——愛慕全新禪柔IV運動系列 瑜伽這種古老的身心練習方式,結合呼吸控制、身體控制和冥想來促進身心的健康和平衡,  全新一代瑞虎3x售價5.99萬元-7.49萬元 以真誠之名重塑國民SUV認知 5月19日,以真誠為約,奇瑞與淄博開啟一場雙向奔赴。三好國民車奇瑞全新一代瑞虎3x于
全新一代瑞虎3x售價5.99萬元-7.49萬元 以真誠之名重塑國民SUV認知 5月19日,以真誠為約,奇瑞與淄博開啟一場雙向奔赴。三好國民車奇瑞全新一代瑞虎3x于  “柏瓴 以愛之名”巨幕燈光秀,有你,才會更浪漫! 520521這個日子因諧音我愛你被賦予了浪漫意義今年的520521兩個日子正值周末在外出游玩
“柏瓴 以愛之名”巨幕燈光秀,有你,才會更浪漫! 520521這個日子因諧音我愛你被賦予了浪漫意義今年的520521兩個日子正值周末在外出游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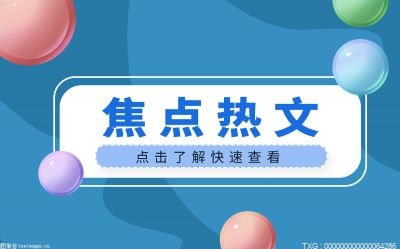 一招短線選股法是什么意思?尾盤買入法的好處有哪些?拉尾盤什么意思? 尾盤買入法:屬于短線的操作,今天買了,明天就有機會賣的。每天下午14:30分的時候有
一招短線選股法是什么意思?尾盤買入法的好處有哪些?拉尾盤什么意思? 尾盤買入法:屬于短線的操作,今天買了,明天就有機會賣的。每天下午14:30分的時候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