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書記》是一部關于書與國際寫作者的訪談錄,將散居在世界各處的作者,以書之名,通過訪談串聯起來。穿梭于問答之間,讀者可以傾聽異域的漢學家如何理解中國,歷史家怎樣梳理歷史背后的脈絡,文學作家如何構思出一部小說,社會學家如何闡釋現代性,童書作者怎樣看待這個世界……本書作者崔瑩暢談創作體驗,與讀者傾情分享《訪書記》的誕生歷程。
 (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
我的“訪書”之旅
2014年秋天,我剛好從愛丁堡大學博士畢業,那時候開始糾結是走學術之路,還是繼續像以往那樣自由撰稿、寫作。我并不排斥做學術,但似乎是一個突然而至的機會,引導我繼續采訪、寫作。當時,朋友轉發給我騰訊文化邀約海外撰稿人的信息。我抱著試試看的心態便投了簡歷,沒有想到的是,當時騰訊文化的負責人張英幾乎是“秒”聯系我,于是,我成為“騰訊文化新聞全球采訪團隊”的一員,這個團隊包括16人,除了來自英國,還有來自法國、日本、德國、美國、阿根廷等國家的自由撰稿人。
我記得在騰訊文化發表的較早的一篇文章是關于英國的圖書王國“海伊鎮”的,那篇文章名為《二手書小鎮古董書賣四千英鎊》。那年冬天,我去海伊鎮淘書,并對“國王”理查德·布斯、格林威斯街角書店老板安東尼、理查德·布斯書店的女主人伊麗莎白和阿迪曼書店的老板阿迪曼進行了專訪。理查德·布斯在寫給我的郵件中寫道:“詩人吉卜林曾經說過:‘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故而兩者永遠不會相遇’,他的觀點是錯的。書籍是國家文化的標識和符號。”冥冥之中,我的“訪書”之旅就此開始。
最初,我的訪談對象主要是來愛丁堡大學舉辦講座的教授,他們同時也是書作者。比如,2015年初,牛津大學當代中國研究學者沈艾娣教授在愛丁堡舉辦講座,解讀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時,乾隆皇帝給英王喬治三世寫的那封“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并不貴重……”的信件。沈艾娣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顛覆了大眾看法。聽完她的講座,圍繞她的觀點和相關研究,我對她進行了采訪。2015年2月,蘇格蘭孔子學院邀請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在愛丁堡大學人文學院舉辦講座,結合講座的內容和最近的中國文學熱點,我對他進行了約3個小時的采訪。當時,王德威教授正在編著《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他在采訪中談到他對這本書的設想:“作者有作家,有學者,有外國人,有中國人。這150篇風格非常不一樣。比如,我邀請美國著名的華裔作家哈金寫魯迅,哈金說魯迅是作家,不能用文學評論的方式寫,所以就揣測魯迅當時的心情,用創作的方式寫了一篇像是小說的文章……”
和漢學家、歷史學家等作家對話,通過騰訊文化這個平臺,把他們的作品、靈感和智慧傳遞給更多人,我覺得我在做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而我自己也有很多收獲。并且,我覺得我很幸運,能夠在和大家分享學者們的博學和智慧之前,先“獨享”。
《訪書記》的誕生歷程
對我而言,做這些訪談最大的挑戰依然是:很多時候——我要自己找到采訪對象,這需要很多毅力。我曾經發微博感慨:“我認為采訪最難的節點是聯系到采訪對象,若對方不回郵件,那就打電話……但很有意義的采訪對象,值得千辛萬苦。”再有一次,我寫道:“編輯大人說:我想到一個好選題,采訪某某,但他是大牛,可能很難采訪到他。我查了一下,果然很難采訪,因為他已經去世了。”
除此之外,我要特別感謝騰訊文化的編輯陳軍吉女士。她從始至終都很支持我的采訪和寫作。她博覽群書,關注文化動態,向我提議了大量和書有關的采訪選題。《狼廳》和《提堂》的作者希拉里·曼特爾、《殯葬人手記》的作者托馬斯·林奇、《證之于:愛》的作者大衛·格羅斯曼和《漫長的訴訟》的作者喬納森·哈爾等人,都是她建議我采訪的。這些訪談都被收入《訪書記》。并且,她還在我采訪前幫我補充采訪問題,完稿后悉心編稿,確保訪談稿的準確和嚴謹。沒有她的鼓勵和鞭策,我不可能完成這么多的訪談稿。如書中所言,“大多數時候,這些對話與訪談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而是整個團隊的努力和付出”。
2019年秋天,四川人民出版社·壹卷工作室的策劃編輯封龍先生偶然看到我的訪談文章,認為它們很有出版價值,便建議我選擇部分進行結集出版。我在咨詢著作權老師的建議后,欣然答應。我希望這些精彩的訪談內容能夠讓更多人看到,希望我的文字能夠以書的形式,留在歷史的長河里。因為,“無論世界多么紛繁,人生如何變幻,讀一本好書,認識一位優秀的作者,總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感謝所有人的堅持,《訪書記》經過8年的歷程,終于在2022年11月誕生。我知道,這本書肯定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缺點,比如我的采訪問題可能不夠全面,書名起得不夠吸引人……但這不能泯滅整本書的價值。“如果你對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如果你想了解那些人與書背后細膩而磅礴的天地,又或者你僅僅是想看看可以讀什么樣的書籍。那么,這本訪談集,都值得你翻開。”
關鍵詞:
 蘋果公司開始對合同工進行裁員?據知情人士透露:公司已悄悄開始削減合同工數量 【 蘋果公司開始對合同工進行裁員 】 財聯社2月17日電,到目前為止,蘋果避免了亞
蘋果公司開始對合同工進行裁員?據知情人士透露:公司已悄悄開始削減合同工數量 【 蘋果公司開始對合同工進行裁員 】 財聯社2月17日電,到目前為止,蘋果避免了亞
 華陽國際:公司目前沒有提供免費設計,也暫未了解到免費設計服務的實質性市場信息-天天熱點 華陽國際(002949)04月20日在投資者關系平臺上答復了投資者關心的問題。
華陽國際:公司目前沒有提供免費設計,也暫未了解到免費設計服務的實質性市場信息-天天熱點 華陽國際(002949)04月20日在投資者關系平臺上答復了投資者關心的問題。
 豐網速運不斷優化服務,提升品質,助力電商用戶提質增效 伴隨著電子商務的進一步發展,我國快遞行業也迎來了大踏步前進。數據顯示,2022年,全國
豐網速運不斷優化服務,提升品質,助力電商用戶提質增效 伴隨著電子商務的進一步發展,我國快遞行業也迎來了大踏步前進。數據顯示,2022年,全國  a2至初奶粉好不好:好消化吸收的奶粉還得看TA 每一代的中國媽媽們都有著自己的育兒經驗,對于崇尚科學育兒的新生代父母來說,他們更
a2至初奶粉好不好:好消化吸收的奶粉還得看TA 每一代的中國媽媽們都有著自己的育兒經驗,對于崇尚科學育兒的新生代父母來說,他們更  爆炸蒸汽深度軟化褶皺,米家手持蒸汽熨燙機全新上線! 你穿什么,你就是什么。人都是視覺動物,任何人遇見不熟悉人的時候,都是通過對方的外
爆炸蒸汽深度軟化褶皺,米家手持蒸汽熨燙機全新上線! 你穿什么,你就是什么。人都是視覺動物,任何人遇見不熟悉人的時候,都是通過對方的外  出彩每一面,吸睛全場面!艾瑞澤8&楊紫聯名紫色車型閃耀上海車展 4月18日,2023年上海國際車展盛大開幕,奇瑞以科技·有愛為參展主題,攜旗下四大品牌
出彩每一面,吸睛全場面!艾瑞澤8&楊紫聯名紫色車型閃耀上海車展 4月18日,2023年上海國際車展盛大開幕,奇瑞以科技·有愛為參展主題,攜旗下四大品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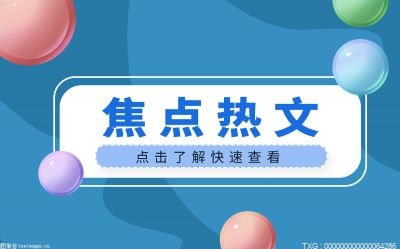 一招短線選股法是什么意思?尾盤買入法的好處有哪些?拉尾盤什么意思? 尾盤買入法:屬于短線的操作,今天買了,明天就有機會賣的。每天下午14:30分的時候有
一招短線選股法是什么意思?尾盤買入法的好處有哪些?拉尾盤什么意思? 尾盤買入法:屬于短線的操作,今天買了,明天就有機會賣的。每天下午14:30分的時候有